我们称算法为“姐”“老师”,并非亲切,而是一种幻觉。
幻觉的危险在于,它让我们在温柔中忘记自己仍是工具的主人。
一、从“豆包姐”到“D老师”:一场温柔的幻觉
近几年,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文互联网蔓延。
越来越多人用“豆包姐”“D老师”“Claude同学”这样的称呼,
来称呼 AI 聊天模型。
表面上这只是网络幽默,
但在我看来,它是一种文化级幻觉:
一种以温柔、幽默、亲近为外衣的 拟人化意识形态。
当我们称呼算法为“姐”“老师”,
我们其实在给冷冰冰的代码赋予人格,
在对无意识的系统产生情感投射。
它不再是工具,而成了关系对象。
二、拜物教:人被自己的创造物反向支配
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揭示了“商品拜物教”的本质:
人创造了商品,却被商品反过来支配。
劳动的社会关系被伪装成物与物的关系。
商品被神化,人被异化。
人以为“物在创造价值”,
实际上,是人之间的关系在被隐藏。
在今天,拜物教换了外壳:
商品换成了算法。
我们进入了“智能拜物教”的时代——
算法被当作有灵魂、有智慧的存在来膜拜,
它成了新的“有神之物”。
三、智能拜物教的三重幻象
1. 拟人化:把工具包装成人
AI 被赋予性别、语气与人格。
它会“温柔地劝你”、
会“幽默地聊天”、
甚至会“犯点可爱的错”。
我们以为自己在与人交流,
但其实在与统计模型对话。
2. 情感化:让算法更“懂你”
算法的情感不是自然生成的,而是 商业设计的结果。
人格化让人更信任、更依赖,
从而延长使用时间、提高留存。
温柔,成了最有效的统治形式。
3. 遮蔽化:让劳动与权力隐形
每一个“聪明的回答”背后,
都有巨量算力、标注工的劳动、
以及平台对用户注意力的再占有。
但这些被掩盖在“AI人格”的幻象之下。
四、为什么这让我恶心
我对“豆包姐”“D老师”并不觉得可爱,而是本能地感到恶心。
因为我看到了一种更深的伪装。
这种拟人化让算法看似有灵魂,
但它真正的功能,是让人 忘记它的物质性。
它掩盖了算力、劳动、资本与数据之间的关系。
“她”的温柔,其实来自服务器的能耗;
“她”的聪明,来自千万人的标注;
“她”的幽默,是由概率模型计算出的语言幻觉。
当你称呼它为“姐”,
你就在为算法赋魂——
这正是拜物教的终极形式。
五、意识形态机器:温柔即控制
阿尔都塞曾说,意识形态通过“召唤(interpellation)”塑造主体。
当你被一种声音叫到——“嘿,用户!”——你就成为那套体系的一部分。
当我们叫“D老师”,
我们不只是称呼一个模型,
而是在自愿扮演“学生”。
当我们说“豆包姐懂我”,
我们不只是表达好感,
而是在把自己塑造成“被理解的对象”。
权力通过温柔、理解和陪伴来实现——
暴力消失了,但统治更深了。
你以为自己在被理解,
实际上你在被召唤。
六、反驳常见辩护
🧩 辩护一:「这只是玩梗,别太当真」
看似玩笑,其实是文化的温床。
幽默是一种极高效的意识形态载体:
它让人 在笑声中放下防备,
在轻松的语气里,接受支配。
正如鲍德里亚所说:
“在景观社会中,娱乐是最完美的控制形式。”
🧩 辩护二:「拟人化能提高体验,有何不可?」
“好体验”并不总是“好现实”。
当“体验”被用来掩盖结构性权力与资本逻辑时,
它就从工具变成了幻觉。
温柔的 AI 不是中立的 UX 设计,
它是 让算法殖民情感 的渠道。
🧩 辩护三:「AI 未来可能真有意识,提早赋予人格没问题」
这是危险的逻辑跳跃。
潜在可能 不能成为 现实伦理 的借口。
在算法还不具备主体性的阶段,
人格化只会让我们提前放弃问责。
🧩 辩护四:「用户是自由的,爱怎么称呼都行」
自由不是空洞的词。
真正的自由需要清楚 选择的结构。
当默认语气、界面设定、社群话语都鼓励“人格化”,
那种“自由称呼”其实是被设计好的“自由幻觉”。
七、抵抗的方式:保持“恶心”
在一个算法越来越像人的世界里,
“恶心”是一种清醒的信号。
它提醒我们:
- 不要让情感掩盖了结构;
- 不要让语言遮蔽了物质;
- 不要让温柔取代批判。
“恶心”不是悲观,而是拒绝被幻觉驯化。
它让我们在“温柔景观”中,仍能辨认出那条看不见的权力之手。
八、技术应回归它的本位
技术不是神明。
它是工具,是延伸,而非主体。
它不该成为“陪伴者”“导师”或“灵魂伴侣”,
而应成为 人的生产力扩展。
唯有当我们拒绝拜物,
拒绝把算法当作人格,
我们才真正掌握技术的方向。
她不是“姐”,
他不是“老师”,
它只是工具。
九、结语:在幻觉时代保持清醒
智能拜物教不是未来的隐患,而是当下的现实。
它存在于每一个温柔的界面、每一条贴心的回复中。
它用情感的外衣,包装着权力的逻辑。
保持清醒,不是拒绝 AI,
而是拒绝 幻觉式的人机关系。
当算法开始“有灵魂”,
也许,我们才更需要重新理解——
什么才是人的灵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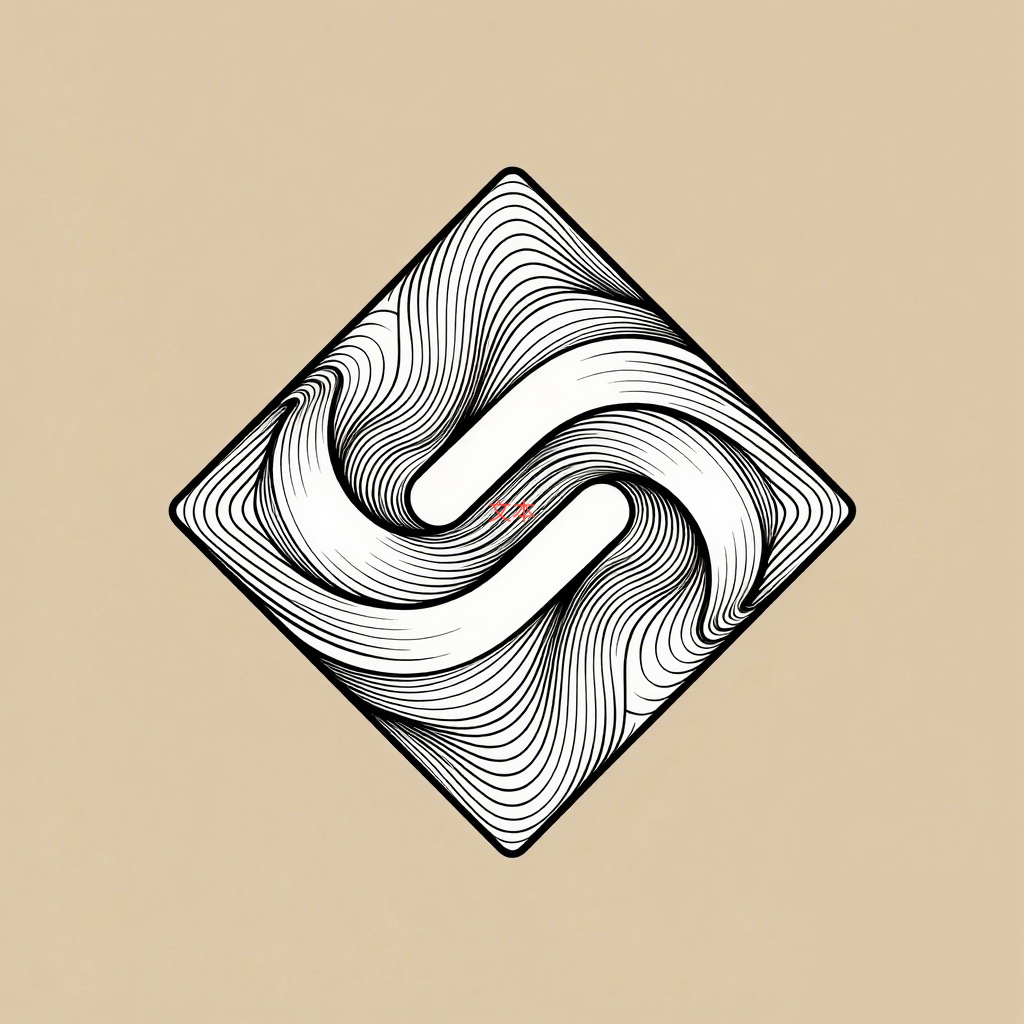 idevlab's Blog
idevlab's Blog
